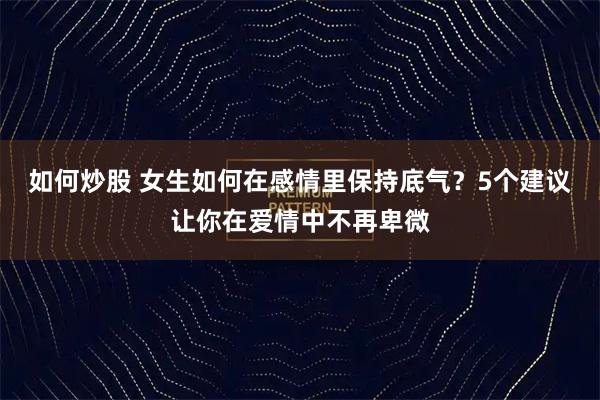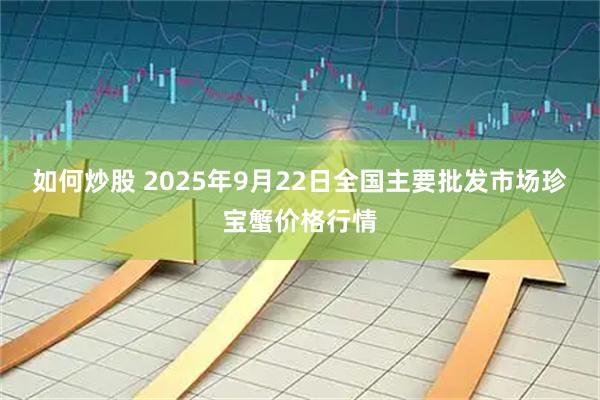*本文为「世界博览」原创内容如何炒股
远方,哈杰尔山脉的轮廓从地平线的薄雾中浮现,嶙峋、陡峭,像一排沉默巨人的脊背,守护着一片不为人知的秘境。
文|小熙
图|dreamstime、视觉中国
像许多从城市出逃的周末,我把行李塞进后备厢,沿着熟悉的E11公路(阿联酋最长的公路,从达夫拉地区到拉斯海玛东部地区)一路向北。车窗外的风景缓慢地变化着,身后是迪拜——一座由玻璃与钢筋混凝土精心打造的“土豪之城”,无数的建筑“奇观”在后视镜中越来越小,直到世界上最高的建筑哈利法塔(原名迪拜塔,高828米)逐渐变成一根刺向天际的针。跨越拉斯海玛(又名哈伊马角)的低矮盐沼,海风开始有了盐与柴油混合的味道。
公路左边的风景始终如一,碧蓝的海水波澜不惊;而右边的风景却变换不断,乌黑的柏油路逐渐被沙粒侵染得有些发黄,平坦的沙漠时不时会隆起几个平缓的沙丘。之后,沙漠与戈壁混杂在一起,散碎的石块上呈现出一种粗粝的、被风和时间侵蚀过的赭红色。远方,哈杰尔山脉(Hajar Mountains)的轮廓从地平线的薄雾中浮现,它们嶙峋、陡峭,像一排沉默巨人的脊背,守护着一片不为人知的秘境。

穆桑达姆半岛位于阿拉伯半岛东北部,北端嵌入波斯湾,隔霍尔木兹海峡与伊朗相望。半岛上是大片山地,植被稀少,海岸线以陡峭悬崖和峡湾为特色。
从阿联酋一路行驶到阿曼
前方,空旷的视野逐渐缩窄,哈杰尔山逐渐占据了前方所有的视线,道路被山脉挤成了小小的一条,车辆就在海与山之间小心翼翼地前行。穿过拉斯海玛不远,就来到了阿里达拉(Al Dhara)口岸,这里的气氛与迪拜的奢华截然不同,空气中弥漫着一种边境特有的混杂气息——汽油、尘土和一丝若有若无的海水咸味。过境的车辆排起了长队,大多是悬挂着阿曼苏丹国牌照的皮卡和旧款越野车。阿联酋的出境检查相对迅速,但是阿曼的入境手续要繁琐很多,护照、车辆保险、车辆证明,边检人员看我不是当地人,还用带有浓重口音的英语问了我几个问题。漫长地等待后,护照上终于盖上了阿曼的印章,一个历史悠久的国度终于向我敞开了大门。

海塞卜是阿曼穆桑达姆省的首府,城市依托天然良港建造,低矮的房屋依山而建,颜色多为朴素的白色或卡其色。
E11公路已经变成了“阿曼02”公路,这里就是阿曼的“飞地”穆桑达姆(Musandam)半岛,它就像一柄利剑深深地扎进了大海,距离对面的伊朗仅仅不到50公里。这条细细的水道,正是全世界最为繁忙的水道之一——霍尔木兹海峡。驶入穆桑达姆半岛,道路变得越来越窄,直到紧贴着山壁蜿蜒前行,刀削斧凿般的哈杰尔山脉好像压在头顶一般,岩石在阳光晕染下呈现出从褐色到金黄的丰富色彩,每一次转弯就像打开一个盲盒一般,谁也不知道下一秒到底是巨石压顶还是海阔天空。在这条壮观的公路前行半个多小时之后,目的地海塞卜的轮廓出现在了前方。
霍尔木兹海峡的咽喉要道
与迪拜的“垂直城市森林”相比,这里更像是一个水平铺开的渔村,低矮的房屋依山而建,颜色多为朴素的白色或卡其色,清真寺的宣礼塔是镇上为数不多的高层建筑。我将车停在海塞卜城堡(Khasab Castle)旁。这座矗立在海岸边的堡垒是小镇最核心的历史地标,也是理解这片土地过往的一把钥匙。上千年前,海塞卜便是波斯湾贸易的重要地区,西亚、印度半岛,甚至北非地区都会来此进行贸易。随着大航海时代的到来,葡萄牙殖民者来到了这里,他们很快意识到海塞卜作为霍尔木兹海峡咽喉的战略重要性,于是殖民者在海塞卜修建了这座城堡,以控制这一地区的海上贸易路线。后来,阿曼当地人推翻了葡萄牙殖民者的统治,但好景不长,这块战略要地又被英国殖民者盯上了,经过了漫长的反抗与博弈,直到1973年英国军队才撤出阿曼。

走进城堡,厚重的石墙隔绝了外界的炎热与喧嚣。与欧洲城堡的哥特式尖顶和复杂雕饰不同,海塞卜城堡的设计充满了实用主义的军事考量:高耸的瞭望塔、狭窄的射击孔、坚固的城垛……如今,城堡内部被改造成了一座小型博物馆,展厅里陈列着古老的炮台、航海图和殖民时期的文物。一块石碑记载了葡萄牙人如何利用这里的天然港湾,垄断香料和丝绸贸易。同时,这里还陈列着当地居民的传统生活用品:捕鱼的工具、采珠的筐子、色彩鲜艳的服饰,最引人关注的是一处传统阿曼房
屋的复原场景,屋内摆放着椰枣、咖啡壶和熏香炉,生动地再现了当地人简单而精致的生活方式。
站在城堡中央那座巨大的圆柱形主塔上,可以俯瞰整个海塞卜,举目眺望,高耸的哈杰尔山脉深入海湾,海平面上,几艘传统的单桅帆船正扬起三角形的巨帆,缓缓驶出港口。它们即将带我进入这趟旅程的真正核心——那片被誉为“阿拉伯半岛的挪威”的神秘峡湾。

海塞卜城堡中传统阿曼房屋的复原场景。
古老的单桅帆船

海塞卜当地人称单桅帆船为“Dhow”,意思是“容器”,这种船最大的特点就是拥有一根或几根高高的桅杆,上面挂着巨大的风帆,这种设计可以使船只更有效地逆风航行。
第二天清晨,我登上了预订好的单桅帆船。这种古老的船型是阿曼海洋文化的活化石,也是印度洋上的一道传奇风景线。这种船在公元前就已经出现了,最初诞生在印度半岛,后来逐渐被波斯湾沿岸的文明所掌握,甚至传到了东非地区。“单桅帆船”这个名称是后来殖民者起的,在当地这种船被称为“Dhow”,学者普遍认为这个称呼来自东非斯瓦希里语,意思是“容器”。这种船最大的特点就是拥有一根或几根高高的桅杆,上面挂着巨大的三角形风帆,据说这种设计可以使船只更有效地逆风航行,后来随着技术发展,方形船帆也逐渐被用在船上。
船主告诉我,在很久以前,这里的渔民就拥有了高超的造船技术,在铁钉普及之前,工匠靠椰子纤维制成的绳子将木板一块块地“缝”在一起,再用鱼油、树脂、石灰的混合物将缝隙填充好。这种技术如今听起来似乎不太靠谱,但一次试验却让人们知道了这种帆船的可靠。
1998年,人们在印度尼西亚发现了一艘单桅帆船的残骸,这艘名为“黑石号”的沉船船上满载着中国唐代制造的器物,据推测这艘船是从阿曼启航,也被称为“马斯喀特的珍宝”(Jewel of Muscat)。2008年,阿曼和新加坡的专业团队按照传统技术,不用铁钉,只用传统材料重新复刻了这艘帆船,在2010年从阿曼出发,历经5个月的时间顺利到达了新加坡,人们这才相信,古老的智慧经得起时间和海洋的考验。当然,今天游客乘坐的帆船已经安装了现代化的发动机,几个人就可以轻松驾驭。我们离开码头,继续向峡湾进发。

1998年,人们在印度尼西亚发现了“黑石号”沉船,船上满载着中国唐代制造的器物,这艘帆船也被称为“马斯喀特的珍宝”。2008年,阿曼和新加坡的专业团队按照传统技术和材料重新复刻了这艘船。
穆桑达姆峡湾与荒废的岛屿
“阿拉伯半岛的挪威”,这个充满诗意的别称,是穆桑达姆峡湾最广为人知的标签。然而,当我真正置身其中,才深刻地体会到,这个比喻既贴切又不完全准确。贴切之处在于视觉上的震撼:陡峭得近乎垂直的石灰岩山壁从海中“拔水而起”,高达数百米,将海湾切割成迷宫般的水道。
这种雄浑、壮丽的景观,确实能让人联想到挪威的峡湾。然而,从地质学的角度来看,两者之间存在着根本性的区别。挪威的峡湾是冰川侵蚀的产物。在冰河时期,巨大的冰川从高山向海洋移动,它们巨大的重量和力量在地面上刨出了深邃的U形山谷。当冰川融化、海平面上升后,海水倒灌进这些山谷,便形成了我们今天所见的峡湾。穆桑达姆的“峡湾”则并非由冰川雕琢,而是地球板块构造运动的杰作。大约一亿年前的板块撞击形成了哈杰尔山脉,新近纪(距今约2300万年至258万年前)的再次撞击使山脉褶皱进一步加深,加上风化与流水侵蚀,让山体形成了很多深谷。后来,随着海平面的升高,山谷被海水淹没,海平面之上的山脊就形成了峡湾景象。
海水在山影的映衬下呈现出一种深邃的、近乎翡翠的绿色。整个世界仿佛只剩下三种颜色:岩石的赭黄、海水的碧绿和天空的湛蓝。而在阳光直射的地方,海水又重新变得清澈透明,从船舷处就可以看到海底的珊瑚,甚至还能看到一些小鱼在船身附近游弋。这里也是非常著名的海豚观赏地,如果运气好,还能看到成群的海豚在船边嬉戏。

船只向东钻进了一条狭长的水道,峡湾中一座荒芜的小岛出现在眼前,这个看起来不起眼的无人小岛在历史上可是赫赫有名,它的名字叫“电报岛”。1864年,英国为了加强与殖民地的联系,决定铺设一条从伦敦到卡拉奇(巴基斯坦重要城市)的通信电缆,因为信号衰减问题,需要在中途建立一个电报中继站,中继站的位置就在这座小小的孤岛上。在这里驻扎的工作人员要忍受高温、孤独和海浪的侵袭,加上高耸的山峰和曲折的峡湾带来的压迫感,让很多人精神崩溃,他们幻想着“绕过霍尔木兹海峡”就可以回到印度,在英语俚语中,“Round the bend”有发疯的意思就源于此。
登上电报岛,发现这里在1869年就被废弃了,如今只剩下一些残垣断壁,除了偶尔有游客和渔船经过外,这里重回荒无人烟的沉寂。但驻足于此,仍有一种与这个小小荒岛不相符的宏大情怀在心中久久不能消散:今天,发达的通信技术让世界上几乎每个角落的人都可以相互联系,而这片峡湾深处,原来藏着全球化最初的一颗螺丝钉。

穆桑达姆峡湾
扫描二维码 ,订阅最新一期世界博览杂志


和业众配资提示:文章来自网络,不代表本站观点。